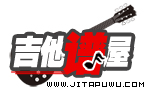连载十四:
“在一次录音结束时,ALAN拎着一把吉他进了控制室,‘这把琴是我从一位本地琴匠那发现的,纯手工制作,试试。’那是一把仿59年LP,漂亮的琴面,没有护板,两个SEYMOUR DUNCAN拾音器。我拿在手里掂了掂,感觉挺不错的。”
“我把琴一插上,那音色真是非常棒,剩下的问题就是找音箱了。我们试了一堆MARSHALL音箱,过程特别繁琐。我记得我们租了每一个可以租的音箱,一个个放在录音室里,摆上麦克,插吉他。我弹几个和弦,听听效果,MIKE和我调整一下音箱上的设置,我再扒拉两下。MIKE会调整一些控制板的设置然后挪动麦克的位置,我再弹几下,我们就这么一遍一遍的试,直到找到最满意的音箱为止。虽然很麻烦,但绝对值。MIKE是一特别好说话的人,他就放开手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我就一个劲的租音箱,试,不满意再退回去换别的。我们试了最少八个MARSHALL音箱,才找到了这个最让我满意的。那感觉就像是上帝帮了我的忙,因为那个我唯一满意的音箱都不是原装的,是被人改装过的。”
“当我听到我的琴从那个音箱里传出的音色,我立马就知道就是它了。和平常一样,我把吉他通上,随意拨了几个和弦,就这么简单。那就是最完美的LES PAUL/MARSHALL组合,吉他音色的深度和音箱失真的脆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听起来太棒了!”
“MIKE突然说‘别动,什么也别动。’他稍微调整了音箱头上的一些设置,然后那音色就听起来更棒了!就是它了,整个录音过程,所有我的吉他和音箱还有麦的设置都没用动过,我们已经找到了最棒的组合,说什么也不能搞丢了。”
“这把吉他从此就一直跟着我。它是由当地MUSIC WORKS店的老店主JIM FOOT生前手工制作的。他一生制作了50把仿LES PAUL,没有一点细节被忽略。有一阵时间这把琴成了我唯一的吉他,在我之后的职业生涯里它也是我在录音棚里使用最多的。虽然在我之后参与的每次专辑制作中听起来都不大相同,但我一直使用这一把琴。这也告诉你录音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录音室房间的大小和形状,录音中使用的控制板,甚至是屋子里空气的分子质量全都和录音最后的效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尤其是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对录音的效果作用非常大。吉他和音箱摆放的位置,麦克的角度和距离,录音棚里存在的任何事物都决定了你录音最后的结果。”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但我很高兴在整个录制过程中我们什么也没碰,所有设备的位置已经很完美了。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自从那次录音之后我再也没能复制当时的效果。这不是把同样的设备摆在不同的录音棚里那么简单,相信我,我试过太多遍了。之后有好多人都对我使用的那个MARSHALL音箱头的数据感兴趣,但没人能复制。我还试过一个按照那个音箱头一模一样改装的MARSHALL音箱,但听起来就是不一样。也不可能听起来一样---因为我不是在当时的录音棚,和当时一模一样的氛围里。那次的录音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速度差不多是一天一首歌;开工的时候给自己做杯咖啡再来点JACK DANIEL’S---还是先喝酒后咖啡来着?---然后开始工作。IZZY的吉他全是一遍搞定----他绝对不可能再次进录音棚从新录一遍,他也不需要:他的演奏技法本身就是特飘,这来一点那来一点,这其实就是一名好的节奏吉他手的风格,如果他反而去花很多时间去修饰一个段子或者不断的录重叠轨,那就是愚蠢了。基本上,IZZY弹的东西都是每首歌曲的心脏部位;如果你把其他所有的音轨都去掉,你就听到IZZY简单而优雅的节奏。”
连载十五:
“作为一个乐队,我们有着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在一起合作。STEVEN会看我的左脚保持速度,他还会看DUFF获得鼓与贝丝配合的暗示。他们两个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交流---他们用眼神来传达每首歌中非常细微变化的讯息。我和DUFF弹着ZEPPELIN风格的单音RIFF,IZZY就用简单的和弦来配合我们的RIFF,但是IZZY的节奏从来不跟我们的节拍,每当我们是重拍时,IZZY弹的是轻拍。所以作为一个摇滚乐队,我们的音乐听起来是挺复杂的,但是核心的东西非常简单。”
“在整个这个录音过程中,有两件事是比较麻烦的。第一件事PARADISE CITY结尾的SOLO,在现场远比在录音室里容易。在演出中,我可以任意决定这段SOLO的长度---一般在1分钟到2分钟内,但是专辑中硬性规定这个SOLO就是30秒钟。让我去把平时的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浓缩到30秒钟挺困难的,当我看到开始录音的红灯亮起时,我突然不知所措了----我居然也有怯场的时候。我记的那天我尝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特别失望,但第二天,我带着崭新的心情回到录音棚,一遍搞定。”
“另一个问题是SWEET CHILD O’MINE。平时都是STEVEN看我的脚来判断速度;SWEET CHILD这首歌是由我的RIFF开始,然后我给他信号把他的鼓点带进来。在第一编录制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在我的吉他响起前加入任何歌曲开始的讯号,所以当我重新坐进录音棚里试着录重叠轨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在猜了:我就坐在那感觉去感觉歌曲开始的时刻,希望我开始弹的时候能和之前录制的合拍。当时还没有数字化的录音技术,那些东西好几年以后才出现的,所以我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讯号。为了这个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反复录了好多次,最后还是搞定了。除了这些小麻烦,整个专辑的重叠轨过程都非常自然,非常快速的完成的。”
“在录制我的吉他重叠过程中,DUFF每天都会来录音棚,既然我已经不粘毒了,我名正言顺的成了酒鬼,DUFF和我就成了酒友。一般都是中午我去他家接他,每天晚上收工以后我们就在街上转悠找麻烦。那会,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猫房(CATHOUSE)。”
猫房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无非就是瞎胡闹呗,但因为提到了AXL所以这一段要加。
“在专辑制作的最后那段时间里,猫房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MOTLEY CRUE的NIKKI SIXX经常在那,所以我在那认识了他。猫房成了我们大家都喜欢聚的地方,甚至连AXL也加入了我们,每次AXL的出现都会吸引来更多的眼球---连我们乐队成员自己都因为有AXL的到来而兴奋,因为他很少和我们一起去酒吧或夜店玩。DUFF,IZZY和我就像下水道里的耗子,而AXL却是更世故些的人,给整个乐队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但每晚的最后,他一般都不会像我们一样闹的不省人事。”
“基本上没天夜里离开猫房,我最后都会在别人家过夜---一般都是不认识的人。绝大多数是女孩,如果我走运的话,第二天一早还可以在她们那冲个澡,然后我开着租的小巴去接DUFF,我们回录音棚开工。那时候就是那个样子---我身上虽然没钱但也混得过去。DUFF和我都穷得叮当响,每天晚上去猫房蹭免费的酒喝前,我们先去麦当劳,用积攒的刮刮卡拼凑出一顿晚饭。你点任何东西它上面都会有刮刮卡,你肯定能中一份免费的署条,可乐或是汉堡什么的。我们就成天吃那个填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