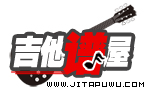连载四十四:
“回了LA我就被安排住进了一家酒店套房。我整个人被刚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折腾得精疲力尽,倒床上就睡了。”
“我起来,发现DUFF就站在床边,‘嘿,哥们儿。。。醒了?’”
“‘嗯,’我说着,同时在想自己现在在哪里。”
“‘穿上点衣服,我就在隔壁房间等你,’他说,‘有些事咱们得谈谈。’”
“我走出了卧室,发现客厅坐满了人:公司的经理,其他乐队成员(不包括AXL和IZZY),我妈,基本上除了毒贩,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在那间屋里。我明白了,他们要玩硬的。我虽然身体和精神还很虚弱,但我看着连STEVEN都TM坐在那等着批判我,他不比我更需要戒毒,他凭什么坐那数落我?我就瞪着他,心里骂着,SB。其他每一个出席的人对我都意味着些什么,虽然我不确定是什么,但肯定有一些意义。基本上每个人还都有话要说。”
“保镖EARL说,‘SLASH,咱们在芝加哥的时候你是那么的充满活力,你那会是那么强壮,我真受不了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妈愣在那看着我一言不发,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ALAN NIVEN还是一贯的直来直去,‘SLASH,你必须进戒毒中心,一切已经都安排好了。’”
“他们都说他们有多爱我,心意我领了。我相信他们是好意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被别人围攻我的性格根本接受不了,所以有些善意也被扭曲了。我完全被孤立到了角落里,平时我用来打发他们的谎话也毫无作用。我没有一点抵抗能力的被他们赤裸裸的攻击,没有开庭就被判了有罪,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任人宰割。”
“我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我妈,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她的主意,她看起来就和当时的我一样不知所措。其他的那些虚伪的混蛋,在我眼里都是TMD道貌岸然的SB!无论怎样,我被判刑了,如果我还想成为乐队的一分子,我就得按规定进戒毒中心。那也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
“戒毒其实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主动想要去戒。你想,就能戒掉----但如果你不想,也许生理上戒了,但心理戒不掉。那就是我第一次戒毒的情况。”
“我被关进了治疗中心,头三四天的依赖反应是最痛苦的,不过还好他们那有专业的医疗设备和辅助药物,所以还不是那么糟糕。我从来都是干戒,所以那次还比较好受些。但还是特别的难受,根本吃不下东西,睡也睡不好,一次睡1,2个小时就不错了。”
连载四十五:
“几天之后,在最初最强烈的那股生理反应开始消退后,我终于感觉好一些,能下地走走路了。那是我唯一能干的事,我根本不想和其他人接触。但我一走出我的病房,一堆医护人员就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拉我去参加他们那的讨论小组。别TM逗了,就因为我能下地走路不代表我愿意和别人扯淡。我尽可能的避免接触其他人,直到我躲在我的病房里饿得不行了才出来找吃的。那就不可避免要碰上陌生人,被迫和他们聊天,那些对话一般都这样。”
“有的陌生人就坐到了我身边,开始抽烟。”
“‘嘿,你为什么进来的?’他们问我。”
“‘海洛因。’”
“一般这词一出口,周围能听见我说话的人最少有一个或者几个人身体出现条件反射似的轻微抽动,抓挠身体。”
“‘是吗,你那不算什么,让我告诉你我是为什么进来的。。。’”
“绝大多数我在里面遇到的人,都有多重复杂的病例,药物还有心理上的。他们就是一帮子社会上最奇怪的个体的集合。就像电影飞离杜鹃巢,我就像里面杰可尼可尔森演的人物一样,坚信我自己是他们中间神志最清醒的一个。我感觉我是完全清醒的,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在做什么事,而那帮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什么,连他们干了什么才进来都不知道。”
“又过了3,4天,我受不了了;我决定了,CTMD!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无论是那帮像苍蝇一样成天围着我转拉我去参加讨论小组的医护人员,还是那些里面认识的那帮子乱七八糟的一次性朋友,我一刻也受不了了。”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缴枪投降。我被囚禁在沙漠之中,暴晒的烈日当头,我根本没法照计划继续在那呆20多天。我告诉那的护士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她想尽了办法想留住我,还把中心的主管给叫来了。”
“主管是一打扮的像新潮西部牛仔模样的人,跟我讲了半天他自己戒毒的经历。他要求我跟他完成剩下的疗程,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接受真正的治疗。他没错,但我才不管呢。我也不相信他讲的他自己戒毒的事。”
“‘我跟你说,’我说,怒了。‘你不能把我拘在这,我告诉你,你没那权利!给我电话还有我的东西,我现在就走人。’”
“‘你正在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你在向毒品投降。你这样是懦弱的表现,你得好好为自己想一想。和我去参加一次讨论小组吧。’”
“‘我哪都不跟你去,’我说。‘甭废话,没门儿。谢谢你的帮助,但是,我TMD要走人了。’”
“我叫了一辆加长豪华轿车来接我去机场,就我一只脚都已经迈进车里了,那个主管还一个劲儿跟着我苦口婆心的想挽留我呢。我坐进了车,把车窗户摇下来看着他。”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你,但你的决定是大错特错的,’他说。”
“‘拜拜了您呐。’”
“车开出去几公里,我看见路边有家卖酒的小店,就叫司机停车。我买了一公升大瓶的STOLI,把盖子揭了一扔,一路到机场的路上抱着瓶子就开始狂灌。我喝得越多,那满腔怒火就越来越膨胀。想着那帮人是怎样当众羞辱我的,把我关进了这么SB的精神病院,他们以为他们会比我自己还了解如何控制我自己,我越想火越大。我都不知道一路上那司机是怎么想的:他刚把我从戒毒中心接了出来,然后就看着我在1个小时内干下了半公升伏特加。”
“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给一我认识的高级毒贩打了个电话,让他在我下飞机的时候就把货准备好。我知道戒毒之后的第一针是感觉最棒的,所以我找了有最纯的货的贩子,不能让我受的那么多罪白浪费了。下了飞机,拿了货,直接回家,爽了。然后我给经理DOUG GOLDSTEIN打了个电话。”
“‘喂?’”
“‘嘿,是我,SLASH,’我说。‘我回~~~~~~来啦。’然后就挂了。”